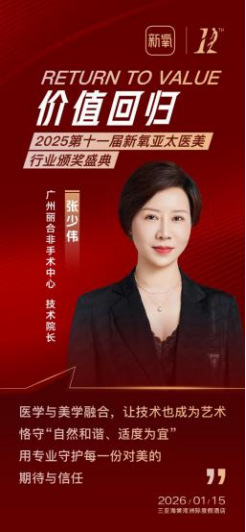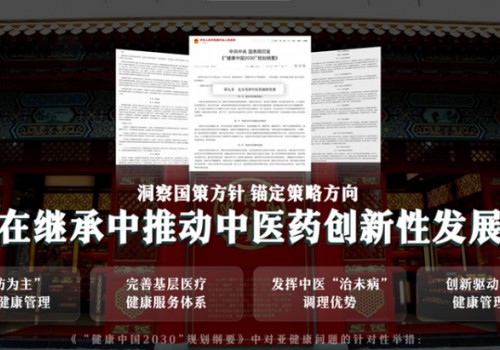(原标题:年度先生 | 刘家琨:投入到中国的混乱中去)
你现在看到的是《时尚先生Esquire》12月特刊“年度先生”专题(点击这里查看年度先生全名单)。接下来我们会陆续推送“年度先生”的封面报道。今天是第8天,主角是年度建筑师刘家琨。
2018年,刘家琨作品西村大院正式投入运营,从精神自由到探讨公共秩序,他不再迟疑,主动投入时代洪流。
“精神幻象”是刘家琨在建筑实践中的追求:不只是实用、功能,或者是风格、手法,建筑可以穿透以上种种,到达新的精神高峰。他无法形容的更具体:“好东西是很难形容的,我也很难表达它。但你站在做对了的东西面前,会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。”
刘家琨:投入到中国的混乱中去
撰文/张洁平 摄影/吴明(Studio6)
来自达卡的精神“确认”
37岁之前,建筑师刘家琨一直觉得自己走了歪路,埋头写小说才是正经事。80年代进大学,“精神性”是他们那代青年念兹在兹的东西,和自己的诗人、画家朋友比起来,他总觉得在建筑设计院的工作太“物质”了,不比文学“澄清”,没有诗歌“惊心动魄”,也不像画画那样“表达自由”。
刘家琨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形容那时“国营单位小职员的沉闷生活”:“伏案制图的老工程师透过汗衫耸起的肩胛骨,使我心头涌起一阵阵莫名的恐慌……”已经做了9年建筑师,但他还没有“打开心里的开关。”1993年,他几乎要转行,但在上海一个建筑师朋友的个人展览上,突然,就被那些并不完美,但才华横溢、野心勃勃的作品击中了。他第一次在那么“物质”的建筑中见到了精神原乡的雏形,同行的好友何多苓、翟永明形容他是“一夜突变”,忽然就从一个摇摆不定的文学人,回到了“建筑人”的路上。
他自己回忆起来,这种更确切的精神“确认”来自遥远的达卡。
20世纪的建筑大师路易斯·康,在贫穷的孟加拉首府达卡修建了他人生中最伟大的几个建筑:国会大厦、国家医院。很多年后,刘家琨都记得他1990年代第一次看到康的房子时的震撼:“恒河泛滥,大地变成一个一个浮岛,植物比人类和建筑更永恒。如果没有一个精神高度,没有信仰,人就不能在那生活。建筑也一样,如果建筑没有精神的高度,也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东西。康抓住了最抽象的层面,达卡的‘原风景’:‘水泛平原,在一片水面上,有一个浮岛’。”
“这个房子就是他们的小庙。其他的都不重要,什么铁皮盖啊,吵闹啊,挂满的衣服堆满的垃圾啊,团团围住,但基本的原风景,就在那里。在一片海上有一片漂浮的东西。”刘家琨形容那是“一个民族、族群、群体的精神幻象”。
“精神幻象”这个词,也成了刘家琨在建筑实践中的追求:不只是实用、功能,或者是风格、手法,建筑可以穿透以上种种,到达新的精神高峰。他无法形容的更具体:“好东西是很难形容的,我也很难表达它。但你站在做对了的东西面前,会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。”
处理混乱后才能得到自由
1996年,刘家琨40岁,在完成了第一部小说作品之后,他终于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,开始专心做建筑。这部小说在建筑师刘家琨功成名就的十几年之后才出版,叫《明月构想》,刘家琨自己形容创作过程为:“有点像运动员上场之前,要去一趟卫生间,把自己想写的写了,然后专心地来做建筑。”
他开始体会到建筑作为一种语言的挑战。“建筑太有用了,太有用的东西要达到无用──而且不是把功能解决了才去──是要在太有用里面,同时达到无用。”在这个过程里,想要实现最后的精神呈现,首先要克服的就是现实操作上的东西,把握住好项目,与甲方沟通,说服甲方,说服施工队,应付这中间所有的扯皮与混乱,“那些最笨重、最艰难的困难,特别像写作里面,你面对结构混乱、理不清、不可收拾的状态,你得正确面对这一部分,不是要陶醉在模型的效果图里,要有能力去解决它,然后才能得到某种自由,去接近本质。”
“但建筑的精神性标准不纯是艺术的。人为什么要盖房子,盖房子就是要用,建筑师要把‘使用’和‘艺术’放在同一个高度。这问题特别繁杂,但也特别结实。你要是不考虑建造,不考虑使用,不考虑行为,你来做一个场景,那是一个永久性布景吧。所以这么想建筑,会越来越有意思。它给你设置了很多限定,很多难题,但你还还是要穿越它,达到某种高峰。”
建筑师刘家琨到达的第一个高峰,是2002年在成都市郊建成的作品:鹿野苑石刻博物馆。这是一个私营的南传佛教石刻艺术博物馆,先有内容策划,后有建筑设计。展览内容的策划者是诗人钟鸣,钟鸣找到了刘家琨,告诉他:“我已经找了你,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事了。”
在很多建筑师看来,这是个难得“自由”的项目:位于市郊,用地宽松,在河滩与树林之间的一块10亩平地,有石桥,有水流,有竹林,几乎没有什么“现实”需要处理,只要建筑能配得上它需要烘托的精神标准。对刘家琨来说,这个相对纯粹的项目,让他有机会抛开杂念,探索建筑本体的问题。而最终,这也结晶成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,也屡屡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美的建筑之一。
一个反高潮的院落
又过了10年,在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住宅、公共建筑、商业建筑的历练之后,已经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的刘家琨,遇到了他又一次的重要挑战。
2012年,他和有“中国最好的甲方”之称的地产商杜坚合作,接下了在成都市区一个巨大的项目。这是90年代从体制内下海的杜坚在手里攥了多年的核心地块,也是向来怀抱文化理想的杜老板,在北漂搞了多年的文化事业铩羽而归回到成都之后,“重出江湖”的第一个项目。
今天回忆起来,两人都会笑着说:“仿佛十几年的相识,就是为了今天这个项目做准备。”和文化产业结缘多年的杜坚,坚持要把这块位于成都西城的空地打造为成都的“西村”──对应纽约东村的形象,一个创意者的社区,创意产业的起搏器。而面对立交密布、高楼林立的城市,刘家琨对这块地的想象则是:院落。一个低矮的、反高潮的院落,是记忆中川西平原的民居院落,也是社会主义时代保留了集体生活的大院儿。
于是,在许多次的争论中,“西村大院”这个名字浮出水面。在刘家琨手中,建筑外形也从纸板模型到实际施工,一点点成型。
那真是一个在高楼中间低洼下去的“院落”。四五层的小楼围出了闭合的一个大圈,中间是足球场、跑道、游泳馆。有人行步道在这交织出的院落空间中凌空飞跃,上下穿行,行走其间,看着这一个平地而起的大“院子”与外面的高楼,会有强烈的不真实感──你很难形容那到底是怀旧的感伤,还是科幻的惊奇。
审美上的体验见仁见智,对刘家琨来说,这个项目的挑战意义在于这大概是他做过最“无中生有”的项目:“鹿野苑是在既有的氛围上做事情,西村周边的情况跟它却是对抗的,是无中生有,什么可以借鉴、发生共生关系的都没有,所以建筑师需要去从无到有建立一个清晰的秩序。”
而跟鹿野苑所对应的个体精神生活不同的是,西村是典型的中国建筑师对公共生活秩序的想象:“鹿野苑就像家,像私人的小园林,像写一个主题鲜明的短篇小说;西村大院从一开始就没有个体诗意的设定,像是要展开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画卷,定义一个公共生活,许多东西需要组织和控制。”
刘家琨承认,这种想象是很“中国”的,甚至很“四川”。他形容这片奇异的巨大院落对应了自己内心的原风景:“一片土地上有一个盆子”,是四川盆地,是杂糅了各种可能性的火锅,也是儿时记忆的院落。
“中国院落、城寨的秩序感是很强的,强于人与人之间的感觉。外面都是灰灰的墙,精彩的在里面,人们是在秩序中自如相处,大家的关系是框定的,这跟中国文化有关。”这种在秩序中自如相处的状态,刘家琨给了一个形象的比喻,“你想象一个人坐在阳台上”。这也是他对自己的精神自况。不是空无一物的自由,而是在一个给定的阳台上独处、看天、与时空相处。
明年他60岁,他形容自己不想置身事外,而是“投入到中国的混乱”,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“精神幻象”,在作品里“传达与时代能量相对称的东西”。
提问个人IP的年代
E:有人说2018年是IP元年,你如何理解作为个人的IP?
刘家琨:独立存在又相互联系。
E:在你所在的行业,5年前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,如今又是什么?互联网和资本正在通过IP改变你所在行业的游戏规则吗?
刘家琨:专业专注吧。互联网渗透了每个领域,都或多或少有所改变。娱乐化社会只会比谁更闹腾,不比谁真好。
E:你觉得你所从事行业的危机是什么?
刘家琨:中国一直以来的高速建设环境(虽然近两年有所放缓)。大部分人都有想得到别人认同的焦虑。
E:请畅想十年后你所在的行业的变化。
刘家琨:或许更多的建筑师或公司以改造旧建筑为主业;而且做更多跨界的尝试,并不局限于传统建筑的模式。
撰文/张洁平 编辑/杨潇
摄影/吴明(Studio6) 统筹/谢如颖
 当代健康
当代健康